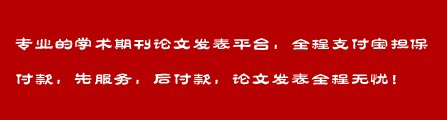某些非正式出版物上的新诗
日期:2010年06月16日 来源:原创 热度:
宁愿搁浅,这在奋发有为的年华,实在是一个悲剧。这样一种精神状态,和我们这一代,和我们的上一代,都是多么的不相同呵!我们前辈们固然有更多的动人的跑步投入战斗的故事,这有待他们自己去叙述。就拿我这么一个没有多少经历的人来和新的一代作比较,也不难指出:我是..
学术论文发表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,它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。在学术发表论文撰写中,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。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,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。在于你选择了什么课题,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。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,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,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,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。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,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,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。
宁愿“搁浅”,这在奋发有为的年华,实在是一个悲剧。这样一种精神状态,和我们这一代,和我们的上一代,都是多么的不相同呵!我们前辈们固然有更多的动人的跑步投入战斗的故事,这有待他们自己去叙述。就拿我这么一个没有多少经历的人来和新的一代作比较,也不难指出:我是在四十年代后期,被席卷蒋管区的学生运动(这是当时全中国的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)带进红色的队伍中来的。我们要民主、要科学,当然就要打倒反民主、反科学的国民党反动统治。目标是清晰的,斗争是义无反顾的。然而,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代,都是在红旗下成长的。对他们来说,地主和资本家只不过是画在纸上的魔鬼。一方面,要民主、要科学的历史任务尚待完成;一方面,他们又懂得,共产党的确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,因为谁都知道,从本质上讲,马列主义正是一切科学的科学,社会主义制度更会带来历史上从未曾见的最广泛、最真实的民主。而不幸客观存在着的,却是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把这一切都搞乱了、破坏了的痛心的事实。有一部分青年由此在政治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,混淆了政治欺骗与革命理想的界限。更多的青年则陷入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,他们失望了,迷惘了,仿徨了,有的甚至踅进了虚无的死胡同而不自知。其中满怀激越,发而为声的,便是目前引起人们注意的某些非正式出版物上的新诗。
顾城同志大致属于这一九。唯其如此,字里行间也就每多愤世嫉俗之言。例如,他有一首题名《两个情场》的诗,这样写道:
在那边,
权力爱慕金币,
在这边,
金币追求权力,
可人民呢?
人民,
却总是它们定情的赠礼。
这里有很大的认识上的片面性。造成这种片面性的,是一段时间我们国家政治气候的异常,这是不能过多去责难青年们的。
众所周知,在人的一生中,青少年时代可塑性最强。他们虽然被极左路线扭曲了,可是我们不能嫌弃他们,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,健全社会主义法制,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争中同他们一道努力,把扭曲了的部分一一加以矫正。如果回到顾城同志使用过的“搁浅”的比喻上去的话,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拉纤、撑篙,或者跳下水去用肩膀将这些小船扛出沙滩和礁丛。我们要消除他们的怀疑和误解,指出国家经过艰苦的奋斗肯定有一个光明前景。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讲,为被玷污了的革命传统平反昭雪才是最大的平反昭雪,为被败坏了的社会主义恢复名誉才是最根本的恢复名誉。
还应当充分肯定的是:这些新的所谓不见经传的诗歌作者,他们的悲欢是和人民大众的悲欢融铸在一起的。他们不仅仅是止于思索,必要时,他们就挺身而出,起来抗争,振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就是有力的证明。仍以顾城为例,他写的悼念周总理的一些诗篇,如《白昼的月亮》、《呵,我无名的战友……》等,就都跳荡着激昂的音符。
现今人们纷纷议论,为父母的都不大了解自己的孩子了。是的,我们和青年之间出现了距离。坦白地说,我对他们的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,也不胜骇异。但是,无论如何,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,理解得愈多愈好。这是一个新的课题。青年同志们对我们诗歌创作现状的不满意见,也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。我们的诗是不是仍旧标语口号太多?当我们用诗来执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使命时,是不是过于僵化?关于诗的艺术规律,关于诗的形象、技巧,是不是太不讲究?我们报刊上的诗的废品和赝品能不能减少一点?这都是可以讨论的。至于青年们的诗歌创作活动,要真想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小路,关键还是在于引导。要有选择地发表他们的若干作品,包括有缺陷的作品,并且组织评论。既要有勇气承认他们有我们值得学习的长处,也要有勇气指出他们的不足和谬误。视而不见,固然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,听之任之,任它自生自灭,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。到头来,灭者固然自灭,生者呢?也许倒会以三倍的顽强,长成我们迄今未曾见过也不敢设想的某种品类。我们是不愿尝这枚苦果的。但如果我们对青年同志没有热烈的阶级感情,就总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征罚。
1979.3.14.北京
(选自1979年10月《星星》复刊号)
《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导言
新诗运动一甲子
本文首发论文邦:http://www.lunwenbang.com
上一篇: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
下一篇: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