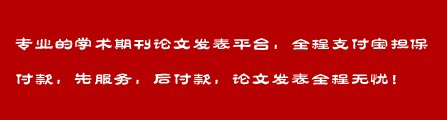诗者,人之性情也。非强谏争于廷,怒忿诟于道,怒邻骂坐之为也。其人忠信笃敬,抱道而居,与时乖逢,遇物悲喜,同床而不察,并世而不闻;情之所不能堪,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,胸次释然,而闻者亦有所劝勉。比律吕而可歌,列干羽而可舞,是诗之美也。其发为讪谤侵陵,引颈以承戈,披襟而受矢,以快一朝之忿者,人皆以为诗之祸,是失诗之旨,非诗之过也。3
这一番话强调了诗歌应当谨守温柔敦厚,怨而不怒的本份,不能为逞一时之心性对人对事痛下针砭。诗人不当“好骂。”这当然是黄氏历久宦海党争之后的远祸之语,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他对诗歌蕴藉深厚,含而不露的境界的向往。这种观点又与杨亿既称诗可“宣布王泽”,又赞义山“寓意深妙”乃是一种不期然之合。
黄庭坚学诗时,西昆体早已式微,其代表作家亦风流云散。那么黄氏从诸多方面汲取杨亿的诗学思想说明什么问题呢?